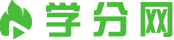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红玫瑰苹果篇一
寒而刺骨的月光无情地撒满寂寥可怖的大地,营造出一种凄凉又孤 叔的氛围。正在我迷茫!无助之际,忽地,我眼前一亮,在那月光撒满的断崖之上,傲然盛开着一朵红玫瑰。
她,玫红色的短发,一副红 色镜框的眼镜后面隐藏着一双炯炯有神, 能洞悉一切事物的黑宝石毁的眼睛,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她的脸庞上,单薄的两片嘴唇却能吐出字字珠玑,妙语连珠,曼妙的身资被一件深邃湖蓝色的呢子大衣罩住,但还是难掩她的成熟性感。这个人就是我可爱可敬的班主任。
开学第一天,我来到了这个陌生但早已耳濡目染的新校园一一民中 。
拖着装载梦想与迷茫沉重的行李箱,把“梦想”放在宿舍后,与舍友就到了教室。来到教室前,我突然愣住了:只见眼前一位气质十足、笑容和蔼的政红色发色的女士,端坐在讲台,随后她从容地转过头笑着对我说:“你好! 今后我就是你的班主任了。我姓汤,那你叫什么名字?”后来我就“自报家门”了一番。在这期间,我一直在用余光默默端详着她,她是那么美丽,是那么高贵,是那么随和。
到了军训,这正应证了句话“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当那炙热的阳光无情地照射下来,让我们的身躯和心灵受到了重度创伤时,我向汤老师投去求助的目光,她用坚定的眼神望着我,那扑闪扑闪的眼睛像在说:“一定要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我读懂了,然后坚定地项着毒辣的阳光,像尊雕像或是像烈火中坚强不屈的邱少云,一动不动。接下来的几天,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我们班的中流砥柱,一个项天立地的女人 汤老师。
不管是在太阳十分强烈的紫外线下,还是在大雨磅礴的阴雨天,她都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们,并把最美丽的微笑送给我们。就像在你最痛苦、难熬之时,别人送一枝娇羞欲滴、 激情四射的红玫瑰给你,你心花怒放、豁然开朗。我们的班主任就像一枝永远不败的红玫瑰, 正如它的花语:热情、活力。在军训联欢晚会前,我们班的节目进行了一次“彩排”。班主任“主动请缨”参与“t台秀”。在她与教官有任何在我们看来亲密的动作时,“观众席” 上片惊呼,当然,我们只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
到了真正上台表演的时候,我本以为汤老师会有些小小的忸呢,哪知她竟走的那么自信、大方。穿者高跟鞋还可以疾步如飞、如履平地。这点是我很崇拜。
其实,她也不是“完美女神”。她也有每个女人如水般柔弱,如泡影极脆弱的一面。
人无完人,如果一个连缺点都没有的“人”,那就不算人。相反,如果一个人能积极乐观地去面对自身的缺点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神”了。而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样一一个 “神”。
那枝红玫瑰在凛列的寒风中,在陡然的断崖上,傲然开放。虽是在断崖上,但它那浓郁的芳香早已布满大地,好像把月光也给染香了。原本月光的寒冷现已被红玫瑰的芳香代替,大地好似苏醒过来了,准备迎接明天的晨光。
红玫瑰苹果篇二
每每想到张爱玲,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永远是那个仰着头,纤腰一把,眼神空旷迷茫的冷傲女子。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那种驾驭文字、描摹心理、营造气氛的能力,至今仍深受人们的追捧,堪称一代才女。张爱玲的书我读过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结局看似圆满,实则浸透苍凉的《倾城之恋》,然后就是那本尘封三十多年,有着明显自传痕迹的遗著《小团圆》。
成年后冷漠偏颇的张爱玲,出生于上世纪初腐朽没落的清朝遗老世家,早年的成长经历,使得敏感而骄傲的她并没有得到多少亲人的情感温暖。与胡兰成相识相恋时,出名较早的她已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女作家。起先,胡兰成从苏青那里读到张爱玲的《封锁》,并对她心生好奇,等到上门拜访她后不久,两人就有了那段虽明显遇人不淑,却让张爱玲高傲的头“低到尘埃里”的爱情。
我们不知道,冷傲的张爱玲曾从胡兰成身上得到过多少情感温暖,但单从后来胡兰成眼中,她的分量还不及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的事实可以看出,张爱玲倾尽全部去爱的这段感情,结局是可悲而又辛酸的,不能不令人替她惋惜和不值,纳闷她怎么会执着钟情于胡兰成那个负心人。
因何爱上一个人,原本就是红尘中的痴男怨女永远无法解答的千古难题,想必就是一代才女张爱玲自己,恐怕也解释不清她对胡兰成一往情深的缘由。但翻开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的《小王子》,我们却还是能从中找到些许有关情感的神秘密码。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它、爱着它,后来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五千朵跟他的那朵玫瑰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才知道,他认为举世无双的那朵玫瑰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这时,狐狸告诉他:人的感情是建立在“驯服”的基础上,在“驯服”之前大家和成千上万的同类并无区别,也不相互需要,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各自来说,对方都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狐狸口中的这种“驯服”同样适用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张爱玲。也许,对张爱玲来说,胡兰成就是她一心一意照料,并被其“驯服”的红玫瑰,所以,即使一再被他玩弄、欺骗和背叛,即使好不容易离了婚,却始终对他牵肠挂肚,甚至到了美国,晚年过着基本与世隔绝的生活时,还写出了那部详尽她自觉卑微爱情的《小团圆》。
佳人已逝,答案再无从可得,但我们知道,张爱玲那段令她本人、令所有人都不堪回首的爱情,早已让她的后半生饱受诟病和伤痛,时至今日,世人真大可不必再苦苦纠缠于她的对与错,还是任由那些如烟往事随风而散吧。
红玫瑰苹果篇三
;是她让我更早地认识了玫瑰的模样。
这是我福分,原以为洼村的坡梁上那些野花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身不由己地摘下一朵又一朵,然后插在发辫上。尽管年少的我们脸上没有可润的护肤霜,那些花朵足够我们成为洼村最美的公主。大人们都是这样夸我们:小妖精。
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因为稀缺才能令人难忘。我也曾无数次地把玫瑰和洼村的各种野花作对比,它是独一无二的。
记不清她是什么时候来到洼村的,更叫不上她的名字。洼村的人都叫她老韩女人。
洼村分上村和下村,中间隔着一座高山。上村居住着汉族,下村居住着回族,洼村有三口水井,供养着上村和下村的家户和牲畜,人们也共同拥护着一个队长。队长脾气不好,人人都畏惧他。队长一生气头就红,吹出的哨音都带着火星子。大家背后都称呼他马红头。
我能背上花书包还得感谢上村的那些女娃娃,她们各个在七岁的时候都去了一个叫学校的地方,那里不仅有钟声,还有琅琅的读书声。我曾偷偷跟随着她们去过那个地方。就一次,我就对钟声和读书声深深痴迷。上村的女娃娃帮我出了好多主意,都不见效。后来,我们家来了一个叫闫老师的女人,她说话的口音不像洼村人。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支援宁夏的知青。父母亲没有文化,说不过闫老师,他们眼瞅着闫老师把我带走了。再次出现在洼村的我就跟往日不一样了,我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学校名,那一年我八岁。
每天晚上,我都要在煤油灯下写字。汉字的香味裹挟着我,我再也闻不到煤油烟尘的气味了。我的母亲时常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关于老韩和他女人的事,都是从母亲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
从我记事起,在村巷里会碰见一个背着背篼的老汉。他中等身材,微胖,皮肤干裂中显现深棕色,戴着一副黑色眼镜,像药店老板拨弄算盘时戴的那种,圆圆的镜片,遮挡着他的眼睛,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定定地看着我,并不发声。我有些紧张。顺着他的眼镜往上看,他戴着一顶黑颜色的帽子,帽子的中间有一个暗红色的圆点。我不知道那是染上去的还是补上去的一块布。还好,在我加快脚步的时候他也转身离去。
后来上学了,每天早晚都会碰见老韩。有一次,碰上老韩,他问我学校名儿叫什么?听那声音浑厚又低沉,我没有回答他,逃跑了。我害怕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行几个人,早早就捏着鼻子,从他身旁溜过去。他会回过头来看我们,背上的背篼太沉的缘故,他弓着背,歪着脑袋,黑紫的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话。因为,我们已经逃远了。
每次见到老韩我既怕他又忘不掉他,好像他身上的气味长有臂膀一样沉沉地压在我肩头上。夜晚的灯光下,由不住地要给母亲说说老韩,老韩奇特的穿戴和背背篼的样子。母亲警觉起来,安顿道,最好离他远点,他可是个厉害人呢!
老韩的棺材是楠木做的,金黄的油漆,晃人眼。老韩不在的夜晚,女人就挨近棺材,仿佛挨近老韩的身体,像能感受到老韩的体温和气息一样。棺材散发出楠木的清香。女人珍惜着,心里格外的踏实,阴暗、静谧的窑洞里,她就能睡去。白天里,在打扫屋子的时候,女人不忘擦拭棺材,一遍一遍。屋里也是有了这样一副棺材而显得亮堂了许多。
棺材是老韩落脚洼村,靠拾粪发家后买的。那个时候老韩才五十岁,女人三十八岁。
老韩是洼村唯一一个拾大粪的人。在此之后,洼村再也没有出现一个靠拾粪发家的人。起初,老韩在洼村拾粪,范围比较小,就守着洼村的地盘。渐渐地,他扩大了面积,去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一去好几天。
男人不在的日子里,女人一个人留在家里,大门上挂着一个大黑锁,好像把他们以往的秘密也封锁了。陪伴她的有几只猪仔,一副棺材,还有园子里的蔬菜和花卉。老韩不在,她偷偷地在园子里埋点大粪,那些蔬菜和花卉就长得好。他们膝下无儿无女。洼村人背地里把老韩叫“莫儿汉”,是鄙视的意思。正是因为这点,女人在老韩面前亏欠万分,低三下四。在老韩的拳打脚踢百般折磨下,女人对他的爱更加地坚固。
她一开始就嫁给了才华。
洼村的那些女人自然是不会理解她的,私下里都说她不仅古怪还是个贱胚子。
女人心里明白棺材是为谁做的,她从来不问。老韩赋予她的任务就是擦拭棺材。她也从未让老韩失望过。每次从外面回来,老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走近棺材,用手摸摸,看指头肚子上有没有沾灰尘。老韩也曾想着把它摆放在别处,但想来想去,觉得放在炕上最合适。炕不是很大的一盘炕,被棺材占去了一大半,剩下的就刚够两个人睡,而老韩睡觉又怕挤,女人就瑟缩在角落里。有了棺椁的存在,老韩更加地冷落女人了,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他总是把脸背过去对着棺椁,偶尔伸手摸一下,嘴里还叨叨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他是很少跟女人交流的,白天的劳累加重了他的呼噜声。
老韩总是扬起头看着灰雾蒙蒙的天空。有一群银色的鸽子在半空飞旋着,飞旋着。
女人消失后,洼村的人都替老韩难过,但不过分悲伤。他们觉得,女人奴隶一样伺候着老韩的吃喝,怎么会弃他而去!对于洼村人的议论老韩保持沉默。他没有放下粪叉去尋找女人。看着他颓废的样子,洼村的人觉得老韩是一个命运悲苦的人。
女人的娘家人应该是不知道的。听说,女人为了嫁老韩和家里人闹翻了,从此一刀两断。在老韩逃离河南一路风尘地来到洼村,老韩因写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深得队长的赏识,留下了他。队长把老韩安顿在上村两孔窑洞里,也就是他们一直住了很多年的那座院落。慢慢地,对老韩的身世,洼村的人略知一二。老韩是个秀才,满腹经纶,在河南那个地方受到了什么迫害,生死未卜。有个好心人觉得可惜,打发他连夜逃跑,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后,一个黄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了洼村的地界。
队长问老韩,除了会写字还会干啥?老韩思谋了半天,没有给出个答案。会种庄稼吗?队长耐着性子问。老韩这回坚定地摇摇头。那你会干啥?老韩说,你给我一个背篼,一个拾粪叉子吧!你想干啥?老韩淡定地回答:拾粪。我一个月给生产队上交三十块钱。队长一听笑了。
一个秀才拾粪,洼村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此,在黎明的曙光尚未开启时,在狗叫声里,洼村的村巷里出现一个黑乎乎的身影。趁着大家还在睡梦中,影子飘进厕所里,不多会儿,又飘进下一个厕所里,幽灵一样。受到惊吓的狗冲着夜空狂吠。
洼村的人养的都是土狗,蹲的都是土厕所。除了拾粪,老韩答应队长每逢过年,出儿嫁女,替人写福字、写对联。
老韩并不向人们解释对联的含义,他手持笔杆,紧锁眉头,神情专注,动作却灵活自如,有种千回百转之意。洼村无秀才,单看红艳的纸张上落下行如流云的草书,那浓重的墨香早已盖过了老韩身上的粪臭味。
老韩把大粪背回家,倒在院子里晾晒,等干了以后指使女人揽进另一个窑洞里,然后上锁,等待吴忠的人来收购。那个时候,我们也才知道吴忠人的口音和洼村又是那么的不一样。听说宁夏吴忠靠黄河边,种的是水田,需要丰富的肥料,而山里的大粪毫无疑问是水田的最爱。经常有吴忠的人开着卡车到山里来收购大粪。他们把洼村人叫作山汉。
老韩说话是算数的,第二个月,他就给生产队上交了三十元钱。马红头乐开了花,他说,还是文化人脑子活啊!
老韩笑了笑,没有说话。
老韩的收益越来越好,有时候从洼村消失不见,马红头也不过问。
晚上,在油灯下,我在田字格里写字。我喜欢灯光下的书写。一旁的母亲拿针将灯头挑了挑,生怕我写错字。其实,母亲还是希望有个会写字的女儿的,只不过,在洼村没有一个上学的回族丫头,她怕被人耻笑。家里没有看时间的表,判断时间的早迟只能听公鸡打鸣。此刻,公鸡睡着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窗外透着灰白,下着雪,也刮着风。偶尔有一片雪花飘落窗前,不一会儿又被刮走了。风雪里,传来一个声音,母亲首先听到了,她停住手里的活,盯着灯芯,目光迷茫中透着一丝哀伤。我也听到了,它细若游丝,仿佛一粒雪片的坠落。我也盯着灯芯。我们企图寻找一种满意的答案。
有几个晚上,我们都会听到那种声音,就那么微弱地附在耳边。有时在前半夜,有时在后半夜,它让我和母亲的夜晚充满了惆怅。父亲时常带弟弟睡另一个屋子,少见和母亲说话,总是阴沉着脸,可是,母亲却从来不说父亲的不是。洼村的女人都这样,以隐忍应对一切。
干冬湿年。每逢过年,洼村都会下雪。
这个时节,上村的家户门口贴着红红的对联,也是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最忙。一个是老韩,一个是屠户乔八子。老韩忙着写对联,乔八子忙着杀猪。
不同的家户对联不同:
发福生财吉祥地 堆金积玉富贵门
楼外海棠肩上月 手中香气笔端诗
春到山乡处处喜 喜临农家院院春
……
洼村的空气里飘荡着浓浓的墨香味,同时,也充斥着凄惨的尖叫声。飞翔在半空的沙鸡子、鸽子惊恐万分,无处落脚。我们这些娃娃追随着它们,希望它们在头顶多飞旋一阵子。尤其是沙鸡子,每年只能相遇一次,而且它們的羽毛太漂亮了。可是,沙鸡子小巧玲珑的样子幻影一般从我们眼前消失不见……我们的伤心是暂时的,大家伙纷纷攀爬上山头。这个时候,这一切被上村的家户尽收眼底。尽管,山头的积雪晃花了我们的眼睛,寒气逼人,我们的衣服里好像灌满了冰冷的水,我们瑟瑟发抖。但很快,快乐塞满了每个毛孔。令我们激动的自然是那些身形滚圆的黑家伙。冬日下,它们各个身上湿滑宛如披着黑色的绸缎,屁股后头一段如肠子一般粗细的尾巴,打着几道弯儿,拧巴着一股劲儿。请来的屠户乔八子,肥胖高大,身着长衫,他手里的刀闪着银光。
不知道是乔八子长衫的作用还是他手里刀光的作用,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从上村回来我就病了,浑身发烫,头疼,恶心,还说胡话。母亲指着我的额头质问道,是不是去上村看杀猪了?我没有承认。安顿了多少回?女娃娃是不能见血的,就是不听!在洼村,有这样一种说法,女娃娃不能见热血,一旦被热血喷了得怪病不说,有可能不来例假,将来不能生孩子。所以洼村的母亲们格外地小心。我们下村宰牲一般请的是阿訇。宰一只羊或者一只鸡都是很讲究的,把它们清洗干净,灌上清水,绑倒在一个浅坑边。阿訇站在宰牲的后面,嘴里默念着什么,还闭着眼睛。这个时候的大人命令我们不能在宰牲的前面去,以防看到鲜血,被热血喷到。
只有一家过年不杀猪,谁?老韩。在上村,浓烈的年味熏陶下,写完福字和对联的老韩,依然背着背篼拾粪。春天来了,有人发现老韩圈里的猪仔又多了几只。那个干瘦的女人,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盆子,里面是她拌的饲料。她走进圈里,招来一阵骚动。她并不急着走开,看着它们吃食,听它们欢叫。在上村,再肥的猪也不及老韩家的。听说,他的饲料是从吴忠换来的,营养价值高。喂完畜牲,女人关了圈门,她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晒着大粪。天空是晴朗的,有微风吹拂着,粪不到一两天就干了。假如下雨或者下雪,女人赶忙把粪揽进去,等待天晴的日子。
初夏很快就来到,阳光金灿灿的。这一天老韩家的大门敞开着。院子中央支着一个长木板。屠户乔八子被请来了。这是乔八子第一次受邀走进老韩的院子。他一边挽起长衫的袖子,一边竖起拇指试试刀刃。老韩客气地递了他一根烟。一根烟没有抽完,老韩已经把一头肥大的畜生绑倒并轻松地放在屠户面前的木板上。乔八子一惊。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怀抱一个硕大的盆子向乔八子走来。确切地说,女人向木板走来,在支架下方放下了盆子。她头发灰白,散乱地披在肩上,在风儿的吹拂下,发丝飘逸,虽说她干瘦,但皮肤细腻,走路轻灵、柔和,似一股风儿到了屠户的面前。待她蹲下身子放盆子的瞬间,一缕发丝滑落下来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女人侧过脸看了乔八子一眼,好像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又把盆子往外拉了一下,走了。她是不打算跟乔八子打招呼的。可是,那种高冷让乔八子过目不忘。乔八子手里的刀子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是老韩把刀子递给了屠户,并友好地拍拍乔八子的肩膀。
当年,那个不凡的夜晚,愤怒的老韩当着乔八子的面,把女人踹进风箱洞里,只听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响之后,洞内无声无息了。老韩转向乔八子,说,兄弟,你没有错,她是个婊子。乔八子想给老韩下跪,老韩没有给乔八子机会。老韩说,我是外地人,惹不起,你走吧,我只求今天的事烂到肚子里,不要说出去,丢人啊……乔八子想救救女人,是我的错,你放过她吧,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乔八子真给老韩跪下了,他还想磕头……老韩微笑着,伸手推了乔八子一把。乔八子像遭到了飙风的吹刮,一阵尘土飞扬后,身子已倒在一棵老榆树下。等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乔八子了。
老韩躺在棺材旁抽了一根烟,刚才的那一掌似乎耗尽了他全部力气,他疲惫不堪,不久便呼呼睡去。
放风箱的那个地方异常安静,人有气没气无法确定,夜又黑了一层,如雷的呼噜声里,已经断裂的骨头开始复苏了。看不到她的头,看不到她的四肢,她蜷缩的有些怪异。她的血脉却接通了,她竟然有了一丝呼吸!
第二天下午,老韩似乎想起来了,或者说,老韩应该想起来了,他总是把时间掌控得恰到好处。在死神想带走她的一瞬,老韩就会立马出现在她眼前。他上前一把将女人从洞里揪出来。
她平展地躺着,四肢慢慢舒展开了,乌紫的面庞渐渐清秀过来。头朝门口的方向,一缕亮光透射进来,她闻到了阳光的芳香,于是,她的鼻翼翕动了。扯断了的头发散落在身边,嘴角的血迹已干枯。一束亮光下,她像汲取了万般能量。
于是,老韩吃到了他喜欢的油炸蛆虫。等把剩下的倒进灶膛,他摔门而去。
院子里剩下女人一个人的时候,她才想起了痛,想起了哭。于是,她可以放心地、好好地哭一哭了,她把许许多多痛苦化作了泪水。一天哭不够,第二天接着哭;白天哭不够,晚上接着哭。在洼村没有人不知道老韩有个爱哭鼻子的女人,却没有人上门劝劝她,安慰安慰她。人们都怕得罪老韩。所以,有些夜晚,我期盼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洼村有很多个夜晚不仅惆怅还是湿漉漉的。泪水是那个女人的解药,也是愈合她伤口的抚慰剂。哭够了,她的身影会出现在圈门口,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盆子。
有一天,一个放羊的老汉说,他在山上看到了两个人。老汉老了,眼神不好,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老汉是这样说的:一个个头高大的男人和一个长头发女人。那一天的天气好极了。阳光明媚,野花飘香,女人的长发在风中飘逸,灰白的发丝染上了太阳的光泽。那一天,她很美。女人对身旁的男人说,谢谢你带我到这里来,有多少年没有呼吸这样的空气了!高个男人说,还是出来走走,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女人笑了,有些感动地伸出双臂,迎着阳光打开了自己,像她三十多岁时那样跟着一个心爱的男人怀揣着无限期盼,跋山涉水、一路风尘……她的激情又复活了。于是她向山梁上喊了一嗓子,韩建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泪水滚滚。高个子受到了感染,他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抚慰道,别怕,有我呢。女人将头埋在高个男人怀里,哭得更伤心了。在他们的身后是起伏的峁山和鲜活的野花。
乔八子从洼村消失了。和乔八子一起消失的还有老韩的女人。马红头带领一帮子人到老韩的家门口,首先看到一个狗头锁子。锁子完好无损,冷漠地注视着人们,似乎在讽刺一个笑话。队长的目光从锁子移开投到老韩的脸上。老韩的脸铁青着。最终,队长的目光掉在了地上。有人拽了队长一下,那意思是说走吧。半路上,拽队长的人说话了,老韩会不会把女人给打死,扔在了井里。
队长派人在三口水井打撈了一遍又一遍,捞上来的除了生锈的水桶、男人的帽子、女人的顶针儿、孩子的鞋子,没有别的。
至于乔八子的失踪,人们还是往好处想,本来人已经疯了,命肯定在,只不过,他自己把自己走丢了,说不准哪一天突然出现在洼村。乔八子的女人鼻子拧成蒜疙瘩。她后悔那天夜里睡得太死,没有看住男人。
书包里玫瑰花瓣早已凋零,失去水分的花瓣边沿开始变黑,花蒂也枯蔫了。那股香味却在,那股香味好像不是从花朵里散发出来的,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发丝里散发出来的。我舍不得丢弃一片,分页夹在书本里。一天晚上,我在灯下写作业,母亲依旧保持着灯下做针线活的习惯。母亲冷不丁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看你还能保存多久?那个女人不是一个人走的。乔八子把所有的人都欺骗了。我愣愣地望着母亲。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她把我看得如此透彻。
老韩是九十年代初搬进乡敬老院的,那个时候他快八十岁,但他身体硬朗,视力好,很少感冒生病。听敬老院的老人们说,他们睡了的时候,老韩的房间里灯还亮着。白天,毫无睡意的老韩从不午休,他坐在第二排八号房门口的板凳上,仰望天空。谁也猜不透他心里想着什么,盘算着什么。他眼角挂泪,鼻涕挂在下巴上。老韩很少跟人交流,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他就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想心事。有风无风,或者下雨下雪,他都要在门口坐着,双手抱着拐棍,看着好像睡着了,当有人走近了,他警惕地睁开眼睛。
那副棺材就摆放在老韩的屋子里,岁月已使金黄变得暗淡无光,落满尘土。
责任编辑 陈少侠
相关热词搜索:;【本文地址:http://www.pourbars.com/zuowen/3065357.html】